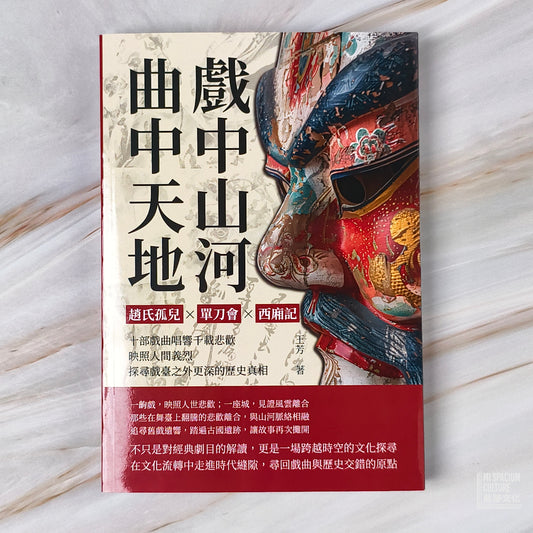序
綜述 把它寫在歷史縫隙裡(節錄)
多年歲月的蹉跎中,戲是戲,歷史是歷史,它們是不相交的兩條線,這種認知直到後來被某種東西反覆擊打。
那年我跟隨香港某電臺節目組的朋友們站在普救寺,看著戲中情景化作具體的場景,以紅牆綠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,心,莫名地一動。我站在鶯鶯塔的暗影裡,看著遊人上下穿梭,聽著導遊認真解說,幻想著真有鶯鶯、張生和紅娘在這裡生活著,他們唱著、演著、哭著、笑著,心頭浸潤著酸酸楚楚的情緒,且越來越濃。想著想著,我忽然意識到,這樣一個大家都知曉的故事,就發生在普救寺,就在黃河邊。
而普救寺在山西。
年輕的時候,經歷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憂煩之後,到了中年,我終於可以撥出時間去看戲了。我站在戲臺下,為《程嬰救孤》裡的義士之死而落淚。那時候的程嬰在我眼裡只是戲曲人物。當我在雜誌社任職後,某一年刊物有系統地梳理晉國大歷史,在不斷翻飛的浸透墨香的紙頁間,趙氏孤兒之事突然從晉國歷史中單獨冒出來,越過紙頁,穿過千年的時光,與舞臺上的精采合而為一。趙氏孤兒就發生在晉國。
而晉國,是山西曾經閃耀著青銅光芒的霸主輝煌。
京劇《寧武關》演出時,我曾被受邀觀看。戲中人周遇吉的悲慘悲壯,縈繞在劇場裡,襲擊著被傳統文化濡染的我。小小一地的人,小小的一座關城;烙印著家國情懷,烙印著國家的傳統精神。
那時,寧武關的面目還是模糊的,但不妨礙我們從歷史中打撈它,它是山西長城的一段,是三關(偏頭關、寧武關、雁門關)之一。而有關寧武關的故事,連帶著關城,還有關城吹來的風,組成萬里長城的寂靜一隅。
寧武關也在山西。
這些訊號,在某一個夜裡,像戰鼓敲起,咚咚咚,一聲聲敲醒我心裡的文字,它們一直在暗夜裡自由組合,想在某一個時刻跳出我的身體。
許多次這樣突然發出的感嘆,在我心頭不停疊加時,就已經不是簡單的加法運算了,我意識到,我生身立命的三晉大地,很偉大。
我要寫它,必須寫它。
正苦苦尋覓題材的我,如獲至寶。
我連忙在心中勾勒出曾經看過的所有的戲,翻閱與戲劇有關的書,走訪相關文化學者。勾著、翻著、走著,發生在山西的戲,這條線越來越清晰,也越來越讓我感慨──大部分流傳久遠的戲,竟然都發生在山西,或者與山西有關。
這是個讓我畏懼的結論。
畏懼,在於這種資訊量的龐大;畏懼,在於劇目流傳之久遠;畏懼,在於我自己蘊藏之淺顯。
畏懼,並不會讓我卻步,只會堅定我的信念,只會疊加我寫作的虔誠。
第一步,先搜尋所有劇目,對自己的寫作目標有所確立和思考。劇目太多了,基於渾厚莊重方面的考量,我刪掉了所有的新編戲,只留下了傳統劇目。
剛開始的時候,民國之後的戲都不在我的考慮之內,因此,龐大的劇目就被我刪掉了一半。繼續篩選,沒有歷史意味的,比如《鐵弓緣》,放棄;沒有旅遊景點可依託的,比如《打金枝》,放棄;既沒有歷史淵源也沒有景點依託的,放棄。隨後,流傳不夠廣泛且不常演的,比如《戰高平》、《火燒綿山》、《汾河灣》,也被我刪掉了。挑挑揀揀,最後就剩下了我寫下的這十部戲。
劇目確立後,開始付諸行動,由兩個方面著手。
其一是尋找相關史料,即從歷史中篩選。一部部關於山西歷史的書,關於戲曲史的書都被我翻找出來,家裡的茶几、沙發、窗臺、小床到處堆滿了書,有的只是一鱗半爪,那也不能放過。歷史這條線,以雍容敦厚之名跳躍著等我檢閱和索取。
其二是走到實地去,即從地理中提取。一個個景點被我找到,山西表裡山河的地理形勢以戲的方式切入,去過的地方還得再去,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新的發現;沒有去過的地方,更得涉足,必須仔細尋訪和傾聽。蠻荒野地的詩情、孤墳衰草的荒涼、殿宇樓閣的莊重、山川河流的雄壯、長城傾圮的滄桑,一一鋪陳在眼前,各有各的敘述,各是各的承載。我把這些一一打包,攬入行囊,背在背上,沉甸甸地行走了半年。
慢慢地,歷史和地理匯成一股清流。地理,是歷史的具體衍化;歷史,是地理的抽象彙總。歷史地理的融合,又化作我心頭的情感,直到噴薄而出。
篩選和提取,自有妙遇。